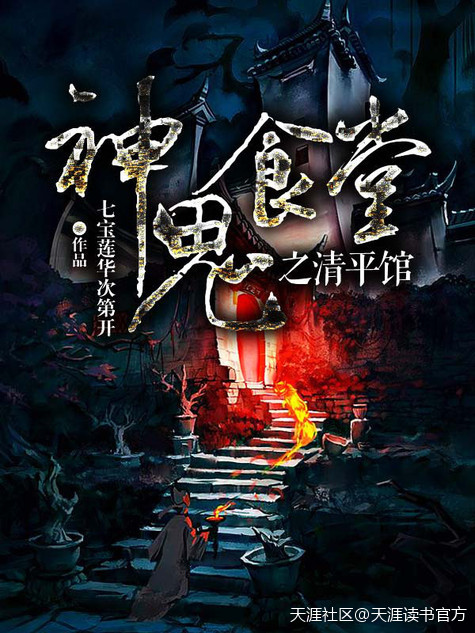第一百九十回隻恐夜深花睡去,不怕毛猴撓腳來
東安市場附近的一條胡同裡,有一戶不起眼的跌打醫生藥鋪。
一進的四合院,院子裡有一棵老槐樹,樹下一張桌子,旁邊坐着藥鋪的少東家,少東家拿着一個木盒子,眯着一雙寶石眼,笑嘻嘻地看着西廂裡門簾子一動,走出一位該飽滿的飽滿,該纖細的纖細的嬌小少女。
嬌小的藍衫少女把一包曬幹的玉蘭花兒骨朵兒放在桌子上,雙手托腮看着桌旁坐着的寶石眼少年:“你這是要幹嘛。
”
“你往後點,吓着你麻着你我可不管。
”說着,少年拿出了一盒子東西,打開一看,全是蟬蛻。
蟬蛻的蟲型密密麻麻的一盒子,果然那少女呀地一聲往後退。
少年笑着将那盒子蟬蛻倒在了桌子上,那一盒子的品相都不好,有的碎了,有的過了色,少年挑揀着,拿着鑷子細竹簽子之類的工具,一點點把那些蟬蛻的鼻子腳爪當做腦袋四肢黏在木蘭花骨朵上,一會兒的功夫,幾隻栩栩如生的小猴兒一樣的玩意兒就出現了。
少年又拿了細鐵絲之類的雜碎彎了一個三輪車,敲了敲桌子,笑着看着少女:“我說藍兒,你不是能讓植物活過來麼,讓這些花骨朵兒活了吧。
”
“喔,好的。
”少女也猜出來少年要做什麼,輕輕一揮手,那些小猴子就活動起來,伸胳膊伸腿兒,然後一個大的騎車,幾個稍微小點兒的叽叽喳喳爬上了車鬥。
“老元啊,這些小東西能跑多遠哪。
”少女問。
少年手裡不停,已經做了十幾隻小猴兒:“這東西叫毛猴兒,是四九城的手藝玩意,體輕能乘風,而且但凡叫猴兒的,都精怪,沾了花骨朵兒的光,這些毛猴兒能當我們的傳信兵呢。
”
少女伏在桌子上,看着少年手指靈活地一會兒做一群毛猴兒,一會兒又給他們做了小車小鬥小桌子小闆凳,各個精巧可愛,忍不住品評把玩,出個主意搗個亂,叫着這個偏了那個應有個帽子。
少年隻是笑着應,倒找了些紅紙裁切了遞給少女,又用竹簽子做了幾個傘骨,拿紅紙蒙了一個:“幫我把這些傘骨蒙上吧。
”
少女嗳了一聲,舉着比一個芋頭大不了多少的小紅傘,嬌憨一笑,袖口一隻毛猴兒竄上來,抓住了傘柄,咻地一聲,便乘風吹去。
“嗳嗳!
跑了!
”少女跳着腳。
“哈哈哈哈,沒事,就是讓他們跑了才對。
”少年一擡頭,雲光落在眼裡,仿佛跌落滿目碎星,分外璀璨。
日光流轉,自東移南,便有風茂少年,綠鬓相陪,藍顔笑看,若夢時光不覺飛,飛光翩來更勸酒。
一陣晌午的暖風吹來,那些毛猴兒紛紛蹬車拉鬥兒,趁着這陣風,迎着晌午的日頭,飛往了白雲綠水畔。
這一日是周末,上午今昭拉了玉卮在院子裡打了一會兒羽毛球,下午就閑了下來,門房說鼓樓那邊來了雜耍和拉洋片兒的,帶起了一路上都是市集,可看慣了好萊塢大片3D效果的,為了拉洋片兒,那也委實懶得動。
到底是玉卮說,不如趁着今天沒事兒,去把自來水筆修一修。
德國産的自來水筆是鍍金頭的貴物件兒,玉卮這一杆不巧碰壞了,筆尖兒劈了,今昭想了想,幹脆也踹了些錢,打算買點兒好玩的東西。
東安市場一帶,布局着好些手藝人、工匠師傅、彩件兒物件兒修理師傅、锔鍋锔碗的補皮襖擦古玩的,還有好些賣小雜貨的,倒是帶着附近食堂小館兒也不少。
修自來水筆這手藝這些年才有,師傅往往兼着修理鐘表首飾。
那鋼筆尖兒到了師傅手裡,拿着一個鑷子一樣的小工具一嵌,擰了兩下,又用一套小掃把小刷子一樣的東西把鋼筆仔細擦了擦,筆縫兒裡的墨迹都擦得一幹二淨,再用絨布統攏一遍,修好了給玉卮,就跟新的一樣。
玉卮付了錢把自來水兒筆放進了軟羊皮筆簾裡,剛一放,就看見什麼東西灰團兒一樣飄了過去。
“怎麼了?
”今昭相中了對面一家賣西洋筆的文具店,正打算過去瞧瞧。
玉卮偏了偏頭,覺得自己眼花,擺擺手:“走吧。
”
東安市場不如琉璃廠,有着些文玩鋪子博古意趣,在東安市場的這些店鋪,是市井生活的閑趣,過日子離不開推不得。
因此推着小車賣的小吃,也是這種市井風格,鹵煮火燒炸灌腸,褡裢火燒三不粘,不過這烈日流火,還是杏仁豆腐的攤子最熱鬧。
賣杏仁豆腐的是一位老手藝,也不藏私,當着大家的面兒讓小徒弟把杏仁兒拿小石磨磨碎了紗布擠出漿汁,這邊融了瓊脂,把牛奶白糖加進去,等杏仁漿汁成了凍兒,澆上桂花糖水,就是杏仁豆腐。
老手藝的刀工好,輕描淡寫練字兒一樣的幾下,就把杏仁豆腐劃成了菱形的小塊兒,每塊兒都均勻,放在小碗裡,擺成雪花的六角形,泡在桂花糖水的瓊漿裡,好像白玉坐金湯,又潤又滑又清涼,杏仁特有的芳香和微苦恰好緩解了這天候的日曬。
吃了一碗,今昭待要再買,卻被玉卮攔住:“你歇了吧,少吃點兒。
”
正說着,什麼東西落在了今昭的空碗裡,手指頭尖兒大的什麼東西,好像還會動。
“啊!
”今昭以為是什麼蛾子之類的,連忙把碗放回了案面上,拽着玉卮就跑,渾然未覺得身後一群什麼東西飄蕩着過來,隐蔽地跟在了她們身後。
沿着樹蔭一路走,兩個人也不知道走到了什麼地方,一路倒是老北京的氣象,街邊懶散納涼的人倒比走路的人還多,穿着洗的發黃的褂子衫的爺們扇着蒲扇,盯着膠着的棋盤不知道如何落子。
槐花最後的香氣彌散在空中,有小孩子兜起自己的衣襟,撿了好多花瓣。
“槐花粥倒是很好喝……”今昭目露豔羨,這時候的槐花還能撿來吃,不必太過考慮污染,她順手摸了摸脖子,“不過到處亂掉的花瓣也挺讨厭的。
”
玉卮看了看今昭的腦後,退後一步:“嗯,也對。
”
今昭滿臉狐疑地看着玉卮,覺得有點不對,但又似乎沒有什麼不對。
玉卮又退了兩步。
今昭的肩頭站着好幾隻奇怪的東西,拉着洋車的停着自行車的放好小推車的,一群大概七八隻這種古怪的東西呼朋引伴,叽叽喳喳。
今昭剛要說什麼,玉卮就喊了一聲:“别動!
”
那些古怪的毛茸茸的東西似乎做了一番溝通交流,而後打發幾個往回飛,今昭一擡眼就看見兩隻這種毛茸茸的怪東西小小的騎着兩輛細鐵絲兒彎的自行車迎着風飛了起來。
“這不是毛猴兒麼?
”今昭身為本地人,對這種民間手工藝品還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為什麼這種東西站在你的肩膀你還能如此淡定。
”玉卮站在距離今昭三步之外的地方。
“咦我小時候組織過參觀這個的制作過程啊。
”今昭滿臉無辜,“這不是蟬蛻做的嗎,真的蟬我都敢抓啊。
”
“……”
這群毛猴兒在今昭的肩膀上蹿下跳,太歲看了良久,問:“你們是要跟我們走嗎?
”
毛猴兒們吱吱喳喳點頭。
今昭看了看玉卮蒼白的臉色,拿出自己的手袋:“那你們進來吧。
”
“喔?
毛猴兒?
”
數字爺們幾個圍着書房茶幾上的毛猴兒,表情各異。
朱師傅抱着肩膀站在稍遠一點的地方:“毛猴兒的頭和四肢是用蟬蛻做的,但身體是幹辛夷花苞,這該不會和蔓藍有什麼關系吧。
如果能讓普通的植物變成活物,也隻有蔓藍能做到了呢。
”
“蔓藍的話,應該做不出這種玩意,在看見蟬蛻的瞬間她就應該昏倒了。
”玉卮中肯地表示。
“咦她的本體是植物竟然還怕蟲子,那麼授粉之類的怎麼辦?
”今昭覺得有些吃驚。
“呵呵呵呵~修行的靈物是不會考慮授粉的哦~”酒吞童子晃着手裡的碧螺春。
“啊密斯蔓藍的本體是什麼啊?
”利白薩滿臉好奇。
“我記得是她來自百花谷。
”衛玠側眸沉思,“想來應該是花物。
”
“大約不是牡丹杭菊一類。
”陳清平回想了一下,蔓藍并沒食材的親切感。
“啊這樣的話青婀是青鳥所以你會想到捶雞什麼的嘛?
”今昭看着陳清平。
“不,青鳥不是鳥。
”衛玠搖頭。
“輝騰,咖啡粉沒有了。
”陳輝卿說。
“我說你們啊,這些毛猴兒都快急死了。
”今昭指着在茶幾上忽而疊羅漢,忽而把自行車豎起來騎,一會兒兩隻猴子做驚恐奔跑狀,一會兒又在一起嬉戲,細細看來,仿佛一場猴戲。
“猴子是靈物,因此猴型也通靈吧。
”朱師傅看了一會兒。
“雖然很奇怪,但是這倆猴兒是在演《情深深雨蒙蒙》嗎?
”今昭托腮。
猴戲的劇情已經進入尾聲,似乎表現着兩隻猴子送走了一群猴子,而這一群猴子四處奔忙,太歲非常感動:“到底是兒行千裡母擔憂啊。
”
“昭啊,你的腦洞在需要的時刻,總是變得格外清奇。
”一個懶洋洋的但又非常溫軟的男音響起,一位穿着普通的素色長褂的少年跟着輝騰出現在門口,一雙長寶石一樣的眼睛熠熠發光,那穿得有些泛白泛舊的褂子穿在這少年身上,有一種清雅的貴氣。
少年靠在門口,那是個慵懶的姿态,卻偏偏挺拔,又偏偏一位嬌小的少女從他的胳膊底下鑽了進來,滿臉笑容:“你們還真的在這裡啊,條件不錯嘛。
”
“蔓藍!
”玉卮倒退一步,“告訴我這些東西不是你做的。
”
“當然不是啦,是老元做的。
”蔓藍跑回來抱了抱今昭,又挽起了玉卮的胳膊,全然沒有今昭想象中的分離的不安和重逢的激動。
玉卮用略顯驚恐的表情看了看老元,似乎打定主意,和他保持一定距離。
那些毛猴兒飛旋着漂浮着落到了老元的肩頭,有的與茶幾上的戲班子彙合,有的在老元的肩頭停息下來,抓耳撓腮,猴戲猿啼,熱熱鬧鬧的樣子。
“說起來,你們在這邊的話,一直都沒有見到青婀嗎?
她好像也在北平啊。
”今昭問蔓藍。
蔓藍搖了搖手:“不知道啦,我也是剛回來。
”
“咦?
”也是和玉卮一樣,一穿來就在國外,想了辦法才回國的?
今昭追問。
“剛到北平發現你們都不在,我和老元就去了上海和南京玩來着,我們這邊的身份,是南來的商人之後啊。
”蔓藍挽着今昭和玉卮的胳膊,毫無自覺地回答。
“……”衆人扶額。
“啊哈哈哈說起來你們都沒有感覺嗎時間感的不對勁兒之類的?
”老元一個箭步過來,笑得流光溢彩将蔓藍隔絕在了玉卮和今昭的殺人視線之外。
“一小時後書房集合,詳細說吧。
”陳輝卿說。
“現在就可以啊。
”老元十分積極主動。
“咖啡粉沒了。
”房東大人不開心。
毛猴兒們似乎感受到了房東大人的沉郁心情,幾隻貼着花片兒紙裙的母猴兒聚在他面前的茶幾台面上,遞傘的遞傘,獻花的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