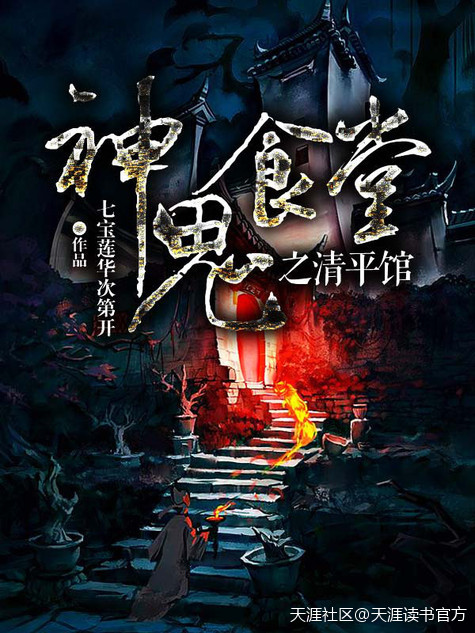第二百零四回美人如花隔雲端,青梅煮酒醉心肝
陳家姐弟的宅子坐落在距離靜安寺不遠,那一片的宅邸皆是安靜的,有種酒香巷子深的低調,一璧的常春藤綠意深深地爬滿了西牆,裡面的宅子有了些年頭,青藤老磚斑駁,即便是這夏日裡,也有蔭涼之意。
朱能垣看了看這宅子,問那聽差:“這是你們後買的房子?
”
聽差點頭:“這是少爺留洋歸來買的,之前的老宅在杭州,大小姐在上海辦的宅子,和少爺辦事兒的地方太遠了。
”
朱能垣嗯了一聲,等到那聽差将衆人引到二樓客房,他才叮囑:“大家在這裡要警醒些了,這房子位于一個巨魔窟驅魔陣陣眼,恐怕期間自有内容。
”
今昭吓了一跳:“巨魔窟驅魔陣?
”一個壓制巨大魔窟的驅魔陣?
陣眼?
她聽利白薩說過這種事情,說是美國那邊就有一個魔窟,因為魔鬼甚衆,所以不得不動用五個城池的布置來鎮壓這個魔窟。
這個五個城池最後都廢了,變成了西部的荒漠,因為壓陣的城池中的人,最終都為一些散露的魔鬼所害。
如果這個宅子鎮着一個魔窟,哦不,這個宅子肯定鎮着一個魔窟,隻看那些魑魅魍魉的數目就知道了。
陳夙蕙到底是華練,不會被魔鬼害死也算正常,但那個陳夙珩——
玉卮倒是聽出弦外之音:“既然如此,那位陳夙珩一介凡人,為何不怕?
”
朱能垣莞爾一笑:“這便有意思了。
”
利白薩唯恐有人聽不懂這個八卦一樣開口:“說起來這個陳夙珩,不僅自小就能瞧見魔鬼,還能驅魔驅鬼,更有手起光落,斬斷魑魅的好本事,偏偏那光,是白光。
”
今昭想起在陳輝卿的記憶裡見過的富貴少爺,冤死女鬼,猥瑣司機,那一場雨夜的橫死,那滴滴答答淌着雨水的屍首裡迸出的白光,恍然大悟:“這麼說,之前那個報恩的女鬼,提示咱們房東大人,華練姐和那一位少爺在一起——這陳夙珩,竟然是——是——”
老元摸着祁紅的樓梯扶手,有些迷茫:“這棟樓的根底結構已經有很多年了,至少是明時的,可這些内置卻是這幾年的新物,如此說來,這棟洋樓是翻新的,可一棟老式宅子翻修成洋樓,破局風水,總是忌諱的。
”
老周靠在二樓的窗子,向外望去,涼蔭下那位少爺正對着聽差吩咐着什麼,以他的視野看去,那沉美靜默的古雅花園之中,蠢蠢欲動着無數殘肢斷臂,那是不知道被什麼東西啃噬後的鬼魅殘餘,那是閱曆如老周這般深廣,亦鮮少見過的情景,什麼人會饑不擇食,去啃吃餓鬼?
忽而視野裡多了一個人,那位陳夙蕙披着一件頗為寬大飄長的紗巾,身後的使女端着托盤,裡面裝着什麼吃喝。
當陳夙蕙經過那些餓鬼殘肢的時候,那些東西紛紛爬纏到她曳地的紗巾上,那位使女受到影響,甚至手有些不穩,可當那個陳夙珩轉身走向他的姐姐的時候,那些餓鬼的殘體,竟然如潮水般退去,又繼續縮在角落裡,暗自觀伏。
“要是桃夭在這裡就好辦了——說起來她到底去哪裡了?
”蔓藍發愁。
“桃夭在此時本也有職務的,或者是與黃少卿一樣,變成了凡人?
”老元摸着下巴,他與老周相視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點非同尋常的意思來——鬼王姬在這個年景裡,是鬧出過一件大事的,别恰好是這會兒吧!
老周的手指指了指這洋樓,老元仔細思忖了一下,無語凝噎。
陳輝卿坐在一樓的客用書房裡,翻着一本從沈鮮衣那邊借來的太歲手劄,這年月裡明晃晃拿出電腦來總是不好,他也閑了下來,沒事翻翻文集古籍,想找到些什麼東西來,解決當下的局面。
手邊的咖啡是牙買加的豆子,昨天陳夙蕙送過來的。
那樣一個人頂着那樣一張臉,穿着居家的裙子,坐在橡木咖啡櫃前面,用手搖磨慢慢磨了豆子,磨得一罐細細的粉,笑吟吟地看着他:“你來試試這個,說是比旁的更厚些,我倒是不太會品的,就寶劍贈英雄了。
”
那眼睛那笑意裡滿滿的喜愛之情,正如昔年一般,她就是那樣一個人,喜歡什麼,毫無掩飾,喜歡的明晃晃響當當,喜歡的昭告天下理直氣壯。
陳輝卿微微牽起嘴角,看着杯子裡的咖啡。
她就算是全忘了,也還是沒變化。
忽然一道若有似無的玫瑰花兒的香氣飄過來,一擡頭,追憶裡的美人端着吃喝乘午後暖煦而來,有風吹起她曳地裙擺,瓊漿玉液般的聲音響起來:“卿卿——”
美人當然是陳夙蕙,那張臉比華練還明豔嬌媚幾分,仿佛是那未曾背負枷鎖的時候,于神居時代的青山綠水之年,肆意笑鬧的少女。
那時候的她,像是沾着露珠的花骨朵兒,有種充滿希望的勁頭。
現在,沒有想到的是,一切都忘了,她的勁頭,卻回到了初起。
陳輝卿放下手裡的冊子,望着那美人。
美人含笑,那裙擺寬而曳地,密密遮住了雙足,可上身卻清涼,露着雙臂心口,半幅噴薄,一地月蜜長霜。
陳輝卿歎了一口氣。
又來了。
美人并不落座,隻是将手裡的盤子放在陳輝卿的手邊,薄胎細瓷含青梅,光輝潤轉盛瓊漿,那是日式的清酒,有種微淺的酸甜芬芳,那佐酒的是幾塊兒清酒心肝,瞧一眼便知道,用的是極鮮嫩的肝髒,白裡泛黃的色澤說明這食料用姜汁湃過才拿酒氣蒸了,去了腥又解膩,密密壓成泥,打了型兒,入口必定也是滑軟的,細細的密密的綿綿的,一抿便化了煙化了水的,就仿佛記憶之中——美人撚起一塊兒心肝,俯身相就,遞到陳輝卿面前。
陳輝卿的視野裡,全然是玉線雪肌,層巒疊嶂,也就沒看見那美人的裙裾下的雙足,不過是一把焦黑枯骨,不成形狀。
美人手裡的心肝,就要碰觸到陳輝卿的嘴唇。
忽然一聲笑,笑得風流迤逦,兩根長指一撩,便将那美人手裡的心肝掠了去,放在自己的嘴裡,還不忘品贊:“确是很鮮。
”酒吞童子舔了舔指尖,“這種水風輕杳的酒香氣,是名為上善的珍品,用來做菜,委實浪費,不過用來配這等未經人事的少年心肝,卻也不枉。
四哥,你以為如何?
”
陳輝卿将擡未擡的手放下去,指尖的白色電光漸漸黯淡,繼而收起。
那美人的眼中閃過一絲驚恐,轉身就跑,可惜那拼湊起來的身軀和手腳在驚慌之下撐不住皮囊,一條殘腿腿骨掉下來,酒吞閑閑起走過去撿起,似笑非笑地看着陳輝卿,随手一擲,将那“美人”懶腰打倒在地,那美人皮忽然就憋了下去,紅顔頃刻成焦骨,酒吞呵呵一笑,擦着手上的灰:“好美,果然是美人。
”
那一地的殘魂碎骨化成幾縷黑煙,咻咻兩聲就沒了。
酒吞童子抖着指尖蹭的黑灰:“你明知道那是什麼,還讓它靠近呢。
這種小小的微不足道的福利,真的這麼令你高興麼?
”
陳輝卿擡頭:“嗯。
”
酒吞童子揚起一邊眉毛,格格一笑:“我在這一點上開始欣賞你了,至少我們病的都不輕。
”
陳輝卿低頭:“棄療。
”
酒吞童子走到那堆黑灰咻咻過的地方,凝眸看着:“低等的魔物。
”
陳輝卿平視:“是。
”
酒吞童子回眸一笑,媚态橫生,指着陳輝卿:“你被小看了。
”
陳輝卿歪頭,一臉迷茫。
端着真正的下午茶等在門口的今昭無語凝噎,轉頭對朱師傅說:“師父,我覺得我又撿着新CP了。
”
朱能垣笑呵呵地看着今昭:“沒事,小鬼小神在我們清平館,都是助攻。
”
一語成谶。
後面的四五天裡,各路小鬼單刷的組團的前仆後繼來騷擾洋樓裡新住進來的這一群人,似乎這些鬼怪殘魂連腦袋都跟着殘疾了,絲毫意識不到這一群人絕非善類,頭一小時披美人皮來勾引衛玠被炸了一個灰飛煙滅,下一分鐘便能幻化美男挑釁玉卮被朱能垣一陣狂風卷走,利白薩每晚必須開啟海神領域把老幾位都罩起來,否則半夜就會有小鬼撓腳,陳清平時常發現吃剩下的東西放在那邊,一轉身的功夫,連盤子都啃掉了沿兒。
晚飯時利白薩按着自己的肩膀:“哎呦,累死我了,我覺得肩膀得了老寒腿。
”
今晚這一餐陳夙蕙不在,去了什麼商界辦的派對,她那個疑似二代轉世投胎的弟弟也跟着去護花,順便捎上了陳輝卿和酒吞兩人。
一場狗皿劇男女主親友團都聚齊,剩下的龍套們便十分愉悅地吃起了晚餐,香水鵝肝,黑虎蝦排,還要陪着火灼的鳗魚壽司和地瓜天婦羅,魚子海膽鱿魚刺身蓋飯。
上海的日式料理極豐富,也有泊來的新鮮食材,陳清平白天出門轉了一圈,晚上就不知道偷了誰家的手藝。
連帶着陳家姐弟也大飽口福,陳夙蕙捏着腰上的肉哀婉,自從族親來了以後,人都胖了。
夜裡月色清冷,魔鬼們更加猖獗,這種淪入魔道的魔鬼,并不是普通的敝鬼符就能屏蔽不見的,所以天一黑,玉卮蔓藍根本就不離開房間了。
不介意看見殘胳膊斷腿的其餘人,會稍微在小客廳聚一下,随意聊聊。
陳夙珩洋行事務忙,不怎麼出現,倒是陳夙蕙幾乎每晚都冒頭,以今昭的角度來看,陳夙蕙頂着幾條爛胳膊身上挂着一半邊兒的鬼腦袋腿上還抱了一串兒焦炭鬼,這種情況下她還能渾然無知覺地跑出來聊天,可見華練是真的忘卻前塵,徹底當了一個凡人。
不過這個凡人不是号稱咖啡玫瑰一直很忙嗎!
為什麼每天都來和房東大人談心啊!
朱師傅摸着下巴對此評論:“即便是投胎轉世,砸碎了三生石,有些人的口味也不會變的。
”
今昭十分無語地看着陳夙蕙,後者眸光閃閃地看着陳輝卿。
那雙眼睛專注地看着正在解釋什麼的陳輝卿,那雙眼睛裡仿佛撒了很多星星的碎片進去。
這位大小姐的目光灼灼好似賊也,一副偷心偷到你眼前的光明正大,正正做到了無事獻殷勤,天天在刷臉。
然而不知緣何,在如此一片有強敵壓頂,有群魔環伺的環境之中,看見這樣毫無遮掩的笑容和溢于言表的喜悅,令人心生向往,無限感動。
那是人間美好的人與美好的情感,美好的綻放。
不懼時間,一如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