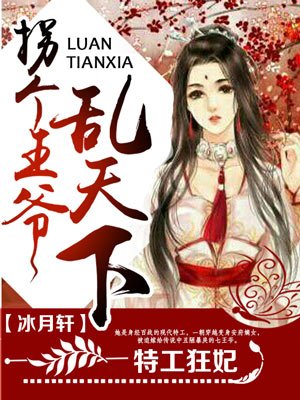史茜妮吩咐吳媽拿一些蜜餞糖果來。
木質的托盤上,滴溜溜地擺33放着紅尖青皮的桃子、像生了鏽的鐵色般的枇杷,另一個羊脂玉的白瓷盤裡,放着徐福記的木棉糖、豐糕,炒的香甜的瓜子。
史茜妮抄起一把瓜子,在嘴裡大嚼了起來,瓜子仁的油膩的脂香混雜着表皮浸過的糖精水的酽甜,着實令她回味悠長。
她大大咧咧的吃在嘴裡,還不忘抓了一把遞到張愛玲的手中。
張愛玲略一嘗了一口,就把瓜子握在手中,橫豎不知該如何是好。
史茜妮瞧料了兩三分,知道她可能吃不慣:“你不喜歡吃甜食?
”
“小時吃傷了胃,蛀了牙,因而我如今不大喜吃太過甜膩的事物。
”張愛玲抿着嘴,猶猶豫豫地說。
“看你的小說中,時常有蜜餞擺在台面上,豐富着書中的角色,還當你是個甜蟲。
”史茜妮笑嘻嘻地沖她做了個鬼臉。
“茜妮”,張愛玲受不了她的熱絡,覺得話題應該回到文學的正軌上來,“你古書讀的多不多?
”
“我爸爸是胡适、魯迅的信徒,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很少讓我讀古書的。
他說自己最後悔的就是少時開蒙的時候,跟着族裡的老先生,讀了不少古書,把腦子讀壞了。
他說中國的知識重感情,西方的重理性,待到他去英國留學時,政治學的書本,如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等”,史茜妮握着瓜子的手指了指遠處書架上的書道,“,他都耐不下性子讀,好一陣子才克服自己的感性思維。
”
“那這倒也難怪,我見你文章中的詞句,外表雖是華麗,可是内中卻立不住足,總給人感覺在水上漂動地蜉蝣的感覺,沒有回味。
”張愛玲撇撇嘴,她這種矜持的女子,做這種可愛的舉動,就如六月裡看見雪景般的稀罕和詫異。
“我打小父親就讓我跟着一個老先生讀古文,從五經到前四史,佶屈聱牙,拗口得要命。
我當時恨毒了父親,他自己成日的抽鴉片煙,捧戲子,偏偏讓我讀那種灰撲撲的書。
”張愛玲說道,“說來也可笑,有一次,約莫着七八歲的光景,我去拜訪一個長輩,他橫躺在藤椅上,花白的胡子垂在兇前,有氣無力地問我有沒有學過詩詞?
我就背了幾十首,當我背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時,他滿是丘壑的臉上黯淡的眼睛裡居然像小孩子一般流下了淚來,抽抽搭搭地在哭泣。
”
“滿清的遺老似乎都是這個調調,一些感時傷世的文章,硬扯到自己身上,讀着讀着就會垂淚,并不悔改自己其實是壓垮滿清的蠹蟲之一。
”史茜妮滿不屑地說。
“話雖是如此,可是當悲劇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時,那種孤寂和落寞,讓人看着多少有些不忍。
”張愛玲苦笑道,“那你看西方的書籍自應是多多的了?
”
“這還用說,這是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的十卷本《約翰・克利斯朵夫》,那邊是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集》,都是我的摯愛,還有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以及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我時時把它們放在床頭,暖洋洋的陽光灑在團花錦被上,讀這些書就如同回憶自己的從前,點點滴滴,斑斑駁駁都在裡面。
那個時候,戰争還是很遼遠的事情,我還不曉得人世間的憂患與苦痛,整個世界就是棒棒糖彩圈的甜心,舔一口,舔一口,都是為了那一點簡單的快樂。
”史茜妮憧憬着。
“可不是嘛,不過我頂喜歡的書都是有點書呆子氣的,像《紅樓夢》、《金瓶梅》、《孽海花》、《海上花列傳》,這幾部書我幾乎都能倒背如流,讀着讀着,時光的影子停滞了一般,在我的書案上,在我的卧室裡,在我的筆端,我可以和童年的我親切地打着招呼,隔着薄薄的一層紙,一層剔透的玻璃,棱角分明的一塊大的玻璃面,閃着熠熠的天光,從前的自己在鏡子裡,現在的自己在鏡子外,觸手可及。
”張愛玲的目中波光流轉。
從她的眼神中,史茜妮知道她是喜悅的,歡愉的。
難得張愛玲有這份自負的舒适。
日光的影子在卧室的牆上慢慢的移動着,從貼在牆上的棕木色書桌,漸漸的移動到黑珍珠般瑩潤的三角鋼琴,再到擺放了文房四寶的方方正正的四角書桌,到了她們玲珑的繡花腳上,窗台下。
一點點憔悴的日色,暈染了整個房間的暖意的對談,這對談中卻有種凄涼的況味。
晚餐吃畢,史筠珩照例離家外出,史茜妮又拉着張愛玲的手,擺弄來,擺弄去,她就像這一雙素手,是如何寫出那種妙筆生花的文字的,怪道呀!
“茜妮,我該走了,你知不知道,我許久沒有這麼的開心。
趕哪天有時間你到我那邊一坐,我在霞飛路上的朝陽弄,來之前記得打個電話,我懶散的要命,沒有朋友來拜訪,我都是懶怠去收拾的。
”張愛玲客套道。
“我讀過你的《公寓生活記趣》,你的生活當真是滿嘟嘟的肉腮的鮮活,哪像我深鎖在大院裡。
”史茜妮有一些怅惘的神情,“幸好,宋主編讓我到《萬象》雜志社幫幫忙,其實我哪有那個本事,幫閑倒還說得上。
”
兩個人嘻嘻哈哈地笑了起來,笑的前仰後合,樂不可支。
笑聲傳到客廳裡收拾餐具的吳媽的耳朵裡,逗得吳媽也微微地莫名其妙地笑了。
史茜妮叫了輛包車,張愛玲等車後,兩人揮手道别,史茜妮忽然文思泉湧,她匆匆忙忙趕回書房,把自己的這番思緒寫下:
“輕輕地你走進我的心扉,
你勾惹起我的漣漪春水,
我躲匿入你的葳蕤絲垂。
歲月在這寂寂的午後,
消散了塵緣的清淚,
何曾暌違?
”
在史茜妮的心中,這份情愫,喚起了她久違的生活的熱切與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