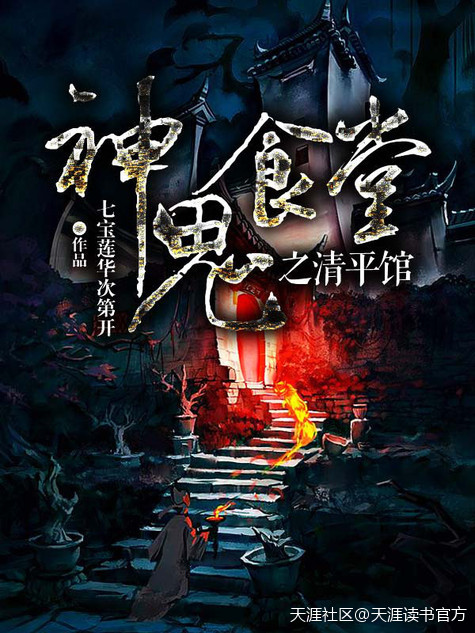第二百三十一回一路梨花香滿路,土裡鑽出黑松露
微星流光,天黑将亮。
守着神道的兩個皇陵衛,身姿挺拔,面容沉肅,仿佛晨光來臨之前的黑暗裡,兩尊守夜的雕像。
那夜色黑濃,夾裹着立秋這日慣來的山岚,在這未來的龍息之地,顯得格外沉凝肅穆。
忽然有一道光,照亮了腳下方寸之地,年輕的那一個忍不住擡起頭,剛要叫,卻被眼前景象驚得呆立當場:
一道光,輕靈,漂亮,有銀銀玉色,像是一尾魚兒,在半空之中遊曳,盤桓于神道之上,久久不去。
那銀魚兒一樣的流光似乎被什麼東西阻隔,無法更靠近墓地神殿一步,隻能在神道上徘徊往來,顯得有些焦急,有些悲傷,似乎那光芒也有神智,在這條路上,癡癡地等着什麼人。
“小尹,你慢慢離開,去叫人。
”年長的那位悄聲吩咐,“就說,有異相。
”
“有異相?
”開封周王府王爺的内書房裡,穿着一身素衣,正提着筆幫她男人的書稿描圖的周王妃馮繁縷嗔怪地扭頭,停了手裡的活計,“是你畫的人身活了,還是昨日寫的書稿,平白多了一萬字?
”
“别鬧。
”穿着家常的衣服,沒個形狀靠着門的朱橚甩了甩手,一貫溫潤如水,靜默如潭的眼睛裡,仿佛挑出了一抹魚兒,甩着尾巴,帶出晶瑩燦亮的波光來,“是那些洋人,帶來一口袋子說極珍稀的香蕈,你瞧瞧,怎麼做了吃了好?
”
馮繁縷這些日子都沒見到朱橚這樣高興過,便也湊趣:“什麼好東西,饞的你,難道還是成精的人參麼?
”
兩口子并肩而行,來到了五味居的小廚房,馮繁縷攬着今昭笑:“我第五房的小妾,今兒你可有什麼好吃的招待我?
”
今昭也是一臉的興奮:“王妃,快來看看,那好吃的,保管你眼熟。
”
五味居的小廚房裡間,朱師傅和老周撐着一個麻布口袋子,裡面有不少的土,兩人正一把一把往外掏着什麼東西。
馮繁縷細細去看,輕呼一聲:“了不得,這是松露啊。
”
那一袋子土裡面是養着的的确是松露,由西洋人漂洋過海把它們帶過來。
老周一邊撐着袋子,一邊伸手去摸,将摸出來的比土坷垃好看不了幾分的松露放在一旁,方便陳清平和朱師傅掂量一下品相。
馮繁縷擰了一把今昭的臉:“果然稀奇,姐可是多少年沒吃過了,當年在巴黎,也就吃了一兩回而已。
”
松露這等上品食材,是入口的黃金。
這種越是金貴珍奇的上等食材,就越要吃它原本的味道。
“黑松露香氣馝馞沉厚,不如白松露霸道,應以微微烤制最佳,待到蕈肉微黃時,那味道最為醇正。
”陳清平一邊看熱鬧一邊說。
清平館衆人曾吃過的鵝肝白露,是白色松露的上品。
用白葡萄酒泡制的鵝肝,在葡萄酒中以溫泉一樣的溫度,緩慢地加熱,做成的凝乳一樣入口即溶的鵝肝,上面撒着隻用火苗兒燎過一下子的白松露碎。
鵝肝的滑膩與白松露那種迷一樣的香氣,簡直是長了手一樣能把人的饞蟲從肚子裡勾出來。
這一次的黑松露,因為是佛郎機人海上順便帶過來的,便挑不了太多的品相,比如那些小頭小腦,大概隻能炖了,或者狠狠心,做醬做粉。
老周一邊掏着,朱師傅一邊按照品相分類,大約分了三堆兒。
陳清平掃過去,眉頭微蹙:“也就隻有三五個能吃的。
”
老宋哈哈大笑:“行!
老大!
我們炖雞的時候你看着!
”
“這東西好吃,不分大小,小的也有小的吃法嘛。
你們天朝上國,吃的太挑!
”利白薩搓着手。
“今兒貼秋膘,炖一隻肥雞,想來不錯。
”蔓藍拍手,“快挑快挑!
”
老周白了蔓藍一眼,依舊一塊兒塊兒往外摸,摸到口袋底子,他眉頭突然一皺,從土裡摸出來一個人頭大小的土坷垃。
那土坷垃順着他的手滾到了地上,撞到朱師傅才停了下來。
“好大的松露!
”朱師傅也忍不住吃了一驚。
那地珍松露骨溜溜從朱師傅的膝蓋旁滾到地中央,說也奇怪,這一滾之下,身子胖大了許多,仿佛剛才那樣團團模樣,隻不過是沒有伸開一身筋骨罷了。
這已然胖大像個兔子的土坷垃停了下來,開始顫抖,活似被人從土裡挖出來,它感覺很冷似的。
隻是片刻之後,一身的土便抖了幹淨。
抖掉了土,那土坷垃已經變成了一個黑毛球兒,跟剛才那灰撲撲的糟爛蘑菇一樣的慫樣子,大不相同。
毛皮雖然有點炸,但到底是絨呼呼的毛兒,就是翹了炸了,瞧着也有幾分惹人喜愛了。
“瞧此物,大約也有兩三百年了。
”陳輝卿猛地提了一句。
連着今昭在内,已經都十分習慣于房東大人這沒頭沒尾的說法風格,隻盯着那毛球。
又是這麼一兩眼的功夫兒,毛球已經像是一隻沒耳朵的黑兔子一樣站了起來,抻了抻身子,張開了兩隻不大的烏溜溜的耗子眼,前肢也伸了出來,這麼瞧着,已經像是沒有喙的大肥企鵝了。
馮繁縷笑,對今昭露出一個“你懂的”的表情來:“這不就是沒腳沒嘴沒圍脖的QQ麼!
”
這黑毛肥企鵝炸着一對兒小眼珠子,噗溜噗溜拍着小翅膀,雖然沒腳,但憑着下盤的肥肉,竟然在地上走動起來!
走到了朱橚面前,打量着他,把翅膀抻得老長,像是皮糖一樣竟然摸到了朱橚的衣襟!
馮繁縷又輕呼:“橡皮果實!
”
奇特的黑毛球摸了摸朱橚的衣襟,而後又把“手”收了回來,噗溜噗溜轉了幾圈兒,看見朱橚已經提筆畫起它自己來,身子一縮,竟然又變成了那支筆的形狀——隻可惜空有形狀,那一身的黑毛色和小眼珠子,還是那樣。
周王妃恨不得以頭搶地——這根本就是巴巴爸爸好嗎!
而且看顔色,還是巴巴媽媽和巴巴伯那一挂的!
“西洋人看來對神異之物不仔細,這樣有趣的生物,都能當做是蘑菇給吃了。
縱然也許一百年才能長出來這麼一個,可這瞧着多神奇多有趣!
”朱橚笑得頗為開心,将那一張速寫收好,“我的書稿,可以再添一樣好物。
唔,算來這等與國朝的人參娃娃地精之類也屬同一族,隻是這變化不如參精精細罷了。
”
“我聽說千年的人參喚作金井玉瀾,能變作極其鐘靈毓秀的人物。
若是我這輩子能見到,那該有多好!
”新手村的太歲一臉神往。
“咦,你不是第一季就見過了麼?
”老宋一邊逗弄着那黑松露一邊說。
“啊?
”今昭一臉愕然。
“金井兒啊。
”老宋漫不經心地回答。
“金井兒?
!
小土豆?
!
”今昭騰地站起身來,差點把她身邊蹲着看巴巴爸爸的周王妃撞翻。
“對啊。
”老宋也很吃驚,“金井玉闌,這不是明擺着。
”
“可是他隻是個土豆啊!
哪裡鐘靈毓秀了!
”今昭炸毛。
“他不是在我們庫裡冬眠呢,等冬眠期結束了,自然出來就是美男子了。
”蔓藍撇嘴。
“說不定等他結束了靈養期,再出來就是絕世美少年,嘛,你們相識于微寒,養成系啊養成系。
”老宋笑得十分開心,冷不防嘴裡塞進來一個又香又沾了好多土的松露,吱吱嗚嗚叫喚,“老大,你幹啥!
”
“抱歉,手滑了一下。
”陳清平拍掉手上的土。
衆人哈哈大笑,鬧了好一陣子,才把那些松露,以及這一隻活物,都收拾停當,約定今晚在五味居饕餮,不醉不歸。
被陳清平嫌棄品相的松露,炖了童子雞。
爐焙仔雞是嫩仔雞做的,增益清補,煮到八分熟後,斬做小塊兒。
再拿鍋裡放稍許油燒熱出肉汁兒,略炒後蓋了蓋子燒到肉汁兒熬盡,加稍許醋酒和鹽,和出肉汁兒再燒到幹,再加稍許,再燒,如此數次,等到雞肉已經酥爛無邊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享用了。
這道炖雞端出來時,滿院子都是醉人香氣,衆人争先去夾,也沒個王法規矩,等搶到朱橚碗裡,便隻剩下一隻腳。
手不夠快的利白薩嚼着另一隻雞腳道:“我以前聽說,這活的松露的皿,可以續命。
老五,你老爹不是病的重了麼,送去給他續命啊。
”
朱橚眼睛一黯:“若是可以,我早就把翡翠天音給他送去,可是如今的皇宮已經是皇太孫的天下,便是我有這心,東西也到不了父皇眼前。
”
事涉皇族内部傾軋,衆人都沒有話說,倒是那個活松露,被混沌和陳夙蕙那隻金華貓追着,球一樣被踢來踢去,發出不滿意的嗚咽聲來。
衆人瞧着三隻奇怪的生物玩得熱鬧,都笑了起來,各自吃飽喝足,端着茶水在五味居各處乘涼,下棋搖扇,閑話品飲,自得其樂。
二十四孝粉絲今昭端了八寶茶打算送去給陳清平,才一走到門口,就聽見朱師傅的聲音:“……魔界業火對于我們八荒中人來說,差不多算是一種蠱,黑龍本身便是蠱蟲,燒盡神鬼為食,增強自己的實力。
你麼,雖然隻是中了一小塊兒,但也的确算是中了蠱,幸好不大,用治蠱草慢慢拔除倒是能的。
隻是,清平啊。
”廚子話鋒一轉,望着陳清平,“我覺得你之前的毛病,和業火無幹。
”
今昭一愣。
和業火無關?
那能是什麼毛病?
她親眼看着業火掉落在陳清平身上的啊。
屋外太歲聽壁腳,屋内男神低下頭。
朱能垣闆着臉全無笑容,語氣也拔得清冷含着冰溜子一樣:“你想要成為什麼人,就要把自己當成什麼人,把你身邊的人,也當成什麼人。
那時候琴曲一響,你的眼神都變了,這并不能瞞住我們。
”
陳清平看了看朱能垣,到底還是開了口:“我想我的身份,你們已經猜到了,雖然我不記得當時我在那邊的事情,但我已經知道,我應該是第一代了。
”
話音一落,今昭捂住了心口,仿佛哪裡有什麼東西狠狠刺了她一般,她要勉強扶住什麼,才能站穩。
陳清平看着窗外秋色薄紅,繼續道:“我與陳夙珩、雀舌的情況不盡相同,既不是投胎也不是附體,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如何,但我感覺到,我的記憶神思,時間與我這皿肉不同。
”
“不同?
”朱能垣猜度,“你是說,你的神思過快,而皿肉并未跟上神思的速度?
還是不契合,不能好好在一起合作?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
陳清平似乎也敲不準這話怎麼解釋,沉默不語。
“反正我們現在遇見什麼都不應該驚奇了。
”朱能垣沉吟片刻又打了一個比方,“你是不是覺得,好像得到了什麼絕世高手的畢生功力,然而自己的身體有點承受不住?
”
“差不多。
”陳清平回想起當時藍光之中,那琴音一響的境況,“當時琴音一響,無數的記憶冒出來……”
“因為被一下子灌了太多的神思記憶,一下子噎住,就僵死閉了氣過去了?
”朱能垣隻覺得不可思議,記憶神思這種東西,還能跟内功一樣,帶走火入魔功能的?
“差不多吧。
”陳清平難得軟弱,去了一身清冷,顯得有些脆弱迷茫。
朱能垣點點頭:“我去和輝卿叔寶商議一下,再艱難,這裡又沒有雀舌,你隻當放假吧。
”說完,朱能垣起身離開,走到門口,看着今昭,淺淺一笑,拍了拍她的肩膀。
今昭剛剛“确診”陳清平的身份,又得知他這是天降神功走火入魔,一時間信息量有點大,還在發愣。
朱能垣手一用力,将今昭推進屋子裡,順便,還把簾子給撂下了。
今昭隻能硬着頭皮端着八寶茶,放在桌子上,低着頭,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種狀況,其實她已經知道了,正如她在那些波濤泛用之中,見到的那張和自己一模一樣的臉。
陳清平見到今昭,怔忪半晌,最後,伸手摸了摸今昭的頭發,安慰道:“我和他們不一樣。
”
的确,他的“過去”他已經不能選擇,但他的“現在”就在這裡,他的“未來”他尚能選擇,他必定會選擇一條不同的路,那條路一定與“過去”不同。
那些曾經發生的事情,将不會發生,那些曾經遇見過的人,也和眼前不同。
兩人相互凝神,一時間氣氛有些異常,今昭剛要開口說些什麼,卻聽簾子一響,青婀一頭鑽了進來,大聲道:“不好了!
朱元璋,死了!
”
今昭一臉納罕:“朱元璋本來就是今年要死的啊。
”這些事情不僅僅是清平館衆人心知肚明,就是周王妃馮繁縷,也是十分清楚的。
青婀搖頭:“不是,不是,朱元璋怎麼都要死的,但是,那玉玺裂開了,砸在了朱允炆的腳上!
”
“啥?
!
”今昭大吃一驚。
那玉玺是朱棣和朱橚的生母宮明玉的玉身,裡面還化了宮明玉的神魂,不說能夠庇佑明朝國祚綿長,也不會現在就壞了啊。
壞還壞在,竟然砸在了朱允炆的腳上。
這句話的信息量有點大,喪事沒辦完,朱允炆還沒登基,也沒下什麼诏書,動那玉玺,是鬧哪樣?
倒是陳清平十分鎮定:“都出去吧,恐怕周王府,要跟着倒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