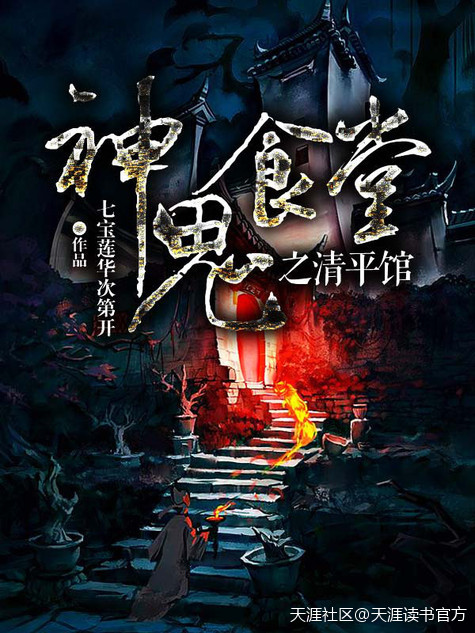第二百四十二回狐裘不暖錦衾薄,西子湖畔花零落
從永福寺下去,一路沿着山階過靈隐寺香火鼎盛的大門,一條路走出去,便是一條路,往嶽王廟去,到了嶽王廟,就是西湖了。
這是隆冬的西湖,剛入夜,薄薄下了一層雪,蘇堤之上,不乏人撐着油紙傘賞雪,白堤斷橋上,更有文士憑橋懷古,看殘雪橋頭。
西湖之水,非嚴寒不冰,冰也不過一層,湖上且冰且粼粼,點點如瓊珠玉屑,有人操小舟敲冰開水路,更是濺起晶瑩片片,恍若星流。
西湖兩岸更是燈火闌珊,一片玉壺光轉,似乎是極其熱鬧的街市。
這番景緻與今昭印象之中夢境的奇異飄渺之美相去甚遠,因太過現實,反而令人覺得恍惚,是不是又一年過去,不過是日子快進了,他們真的就在西湖旁遊賞。
“安心吧,你是歲時十二族中人,這種事情,以後隻多不少。
今日小寒,是祭仁宗的帝龍的儀式。
好多人出來走百病。
僅此而已。
”元夢澤抄着一副漂亮的兔毫繡金的手籠,掏出幾個大錢付了車資,對着蘇堤努了努嘴。
“這大晚上的也不嫌棄冷。
”今昭對各個時代的女子逛街的熱情總是很崇敬。
“她們都是八荒中人,何必嫌冷。
”老周白了她一眼,“你冷麼?
”
說話間,衆人靠近了那一條街市,卻發現這條街市是環湖而起的,從嶽王廟過去可以到曲院風荷,還可過蘇堤春曉。
尤其是蘇堤之上,貼燈謎擺小攤交錯綜合,貴女公子,僮仆執燈,侍婢妾媵冉冉追随。
星月之下,燈輝皎皎如魚龍起舞,紅男綠女,塞街填巷,低言悄語,嬉笑嘤嘤。
時人相信,夜走過橋,可以祛除百病,治療疼痛,因此家家戶戶的女子,都會佩玉簪黃,穿街過橋,提燈相約走百病,足可走上一夜。
以八荒界的說法,走百病的确是真有其事的。
不遠處似乎有歌樓獻藝,袅袅琴音傳來,是一曲《喜相逢》,那琴曲活潑喜悅,帶着少年人特有的天真俏皮,那種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的快樂。
那種眉眼綻放,見到心上人,嘴角都忍不住要彎起來的情緒,感染了街上遊人也喜眉喜眼,年輕的愛侶,相攜而去,買了兩串同心結,各自系在腰間,一塊兒五香糕,掰開分食,一碗雪水煮的梅粥,各自一勺,抵額而食。
“這……”别說是今昭,就是朱橚也不明白,為什麼元夢澤要帶他們來這個地方。
“且走着吧。
”元夢澤依舊笑得十分神秘欠錘。
這蘇堤并不是今昭記憶之中的蘇堤,記憶之中的蘇堤可沒有這樣寬,這樣熱鬧,倒是玉卮吸了吸氣,瞥了朱師傅一眼:“這地方,假兔子那次,我們來過。
你借了路。
”
朱師傅微笑:“是啊,花觀還請我們吃面來着。
蘇堤六橋,我們大約可以再走一次了。
”
過了熱鬧的跨虹橋和東浦橋,便是壓堤橋,這橋下此刻遊船畫舫來回穿往,站在橋上,西湖美景一覽無餘,船上遊人絲竹笑鬧不絕于耳。
“啊呀。
”鬼王姬一聲輕呼,“怎麼回事。
”
她拉着青婀去看景兒,跑在最前面,衆人聞聲圍攏過去,也是大吃一驚。
眼前的熱鬧街市自壓堤橋這一頭便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番春和景明,蘇堤之上,有人負手而立,吟詩作對,有人騎馬而過,意氣風發,還有不知誰家頑童,不過總角,跑來跑去,抱着好大一個佛手在玩鬧。
這一派清風拂面,綠水風流的景象,比起剛才的熱鬧,遜色不少,卻有另一番情趣,讓人不由得想起天真溫軟的小兒女時光。
“那會兒我和她偷偷來過杭州,足足呆了一個月呢。
”朱橚想起往日時光,近年來漸漸清朗澄澈,不染纖塵的目光裡,浣了一捧頑皮和溫柔。
路邊有攤子在賣春茶和陽春面,有歇腳的客人用面裡的白肉在逗貓兒狗兒。
瞧見清平館一行人走過來,微笑颌首。
衆人又繼續走上望山橋,這橋能瞧見三潭映月島,隻見那島上此時似乎有人娶親,吹吹打打,十分熱鬧。
橋上擠了好些狐狸尾巴老鼠臉之類的小妖怪,正拍手叫好,那新郎倌兒騎着高頭大馬,一身大紅,在對面的島上跑馬,極是惹眼。
從望山橋下去,景緻又是一變,過了春日來到夏季。
這一段路楊柳依依,兩側是集市,都聰明地擠在柳樹蔭涼下,賣酸梅湯和濃烏龍茶的攤子隔不遠就有一個,冰珠兒敲了一碗澆着果汁,很似刨冰冰粥之類的甜點。
雜貨貨郎的擔子前面人最多,有買針頭線腦的,也有買珠花水粉的。
還有老婦人挽着籃子,籃子裡青藍色的蛋,惹來好多人驚歎:“這是青鳥?
可能孵活?
”
青婀撇嘴:“扯蛋吧。
青鳥可不是蛋生的。
蛋生的叫做翠鳥,一點兒用也沒有呢。
”
鬼王姬和蔓藍捂嘴笑。
這夏日集市雖然沒有冬日的燈市熱鬧,可透着尋常日子的煙火氣息,也很有趣。
就連朱橚都忍不住東瞧西看,不由得又想起他的王妃:“女子操持家務,要管着這樣多瑣碎的事情,真是難為。
”
朱師傅看了看走在前面帶路的元夢澤,和衛玠對視一眼,莞爾一笑。
酒吞墜在最後面,此刻懶洋洋地指了指前面的鎖瀾橋:“那邊,該是秋天了吧。
”
正說着,利白薩已經跑上了鎖瀾橋,指着遠處靈隐方向的群山:“哎呦!
楓葉!
好漂亮!
”
“哎呦!
楓葉豆沙包!
”陳夙蕙也十分驚奇,可不過是轉瞬,她就露出一臉沉思,“這個地方,我為何如此熟悉。
”
“您老必須熟悉。
”老宋笑得十分意味深長。
走上鎖瀾橋,瞧見的一片遠山金紅層疊,青天朗日,一隊士兵着金甲銀槍而過,老周有點吃驚:“那不是天兵麼。
”
那一隊天兵蕭素走過,卻帶不走楓紅流火。
這一段路霜紅霧紫,點綴成林,影醉夕陽,鮮豔奪目。
有文人雅士,寫紅葉詩箋,臨風擲水。
風清湖白,碧水生金。
忽聞遠處山寺鐘磬,半空梵音,天上仙吟,能滌去人心幻境,還破清明。
也有人在斜陽裡湖上撐舟,任憑浪送風托,随波逐流,烹一壺桂花茶,自得其樂。
“天涼好個秋啊。
”朱橚不知想到什麼,莞爾一笑。
“人生之暮秋,可不是應當了悟了麼。
”衛玠當先一步,踏上了映波橋。
這是蘇堤六橋最後一橋,橋下不遠便是花港觀魚。
登橋看去,又是雪夜霜薄,燈火闌珊的熱鬧,婦人孩兒手裡都提着小花燈。
那燈做的巧,插瓶兒也做的精細,各種植物花朵的枝條上,站着絨布的羽毛的泥塑的各色小動物,有喜鵲登枝,也有黃莺歌柳,鴛鴦銜草,魚戲蓮葉,還有荷上蜻蜓。
陳清平和朱師傅已經在那一家賣燈糕的攤子前面買燈糕,朱師傅介紹得細緻:“花港這家做的最好。
尋常在人間是吃不到的。
”
炸燈糕是一種甜糯的小點心,做法和湯圓差不多,都是糯米的,隻是燈糕要做出燈的形狀,糯米還是太有彈性了,因此加了藕粉進去,既添了幾分清甜,也讓面團顯得硬挺一點兒,把和好的面略蒸到八成熟,拿出來放冷。
裡面包上花兒朵兒果子蜜之類的餡料,捏出兔子燈,荷花燈之類的形狀,在油鍋裡一滾,便滾了一層金燦燦的外衣。
吃起來甜甜糯糯,味道還在其次,主要是樂趣和好兆頭。
陳清平點了幾種餡兒,對那攤主道:“這些打包。
”
老宋和老元湊過來哭:“土豪!
求大腿!
”
朱橚跟在後面,微微一笑。
今昭差點被燈糕噎死。
這人自從馮繁縷過世之後,便一味地鑽研醫理藥學,著書立說,有出世之态,但她冷眼瞧着,那份出世裡面,隐約是有些不甘的。
想來他少年權貴,青年起卻一直被打壓,過的戰戰兢兢,心裡頭當是不服氣的。
不過今兒這蘇堤六橋一過,這人身上有什麼東西,卻發生變化了。
瞧着……像是悟了?
今昭撓撓臉,不知道這景色變幻的蘇堤六橋華燈妖市,能讓他悟出個什麼毛線來。
不過這快要玉成的人,瞧着真好看哪。
今昭花癡臉。
陳清平順手在她的頭頂敲了敲。
一時間衆人吃着燈糕走到了花港觀魚,這裡的花港觀魚是一間極漂亮的酒樓,鯉魚姬來往穿梭,溫酒走菜。
元夢澤也不打招呼,直接走進去進了後院,院落之中有一扇拱月門,門上挂着江水海崖的簾子,簾子裡傳出熟悉的仙音雅樂,清平館的夥計們一聽,就卷起袖子準備進去揍那神出鬼沒無處不在的琴師。
“不行了聽了一輩子,老子很搓火!
”老宋咧嘴道。
“怎麼辦我現在聽見這個琴音就覺得想要現原形!
”利白薩也邪魅一笑。
穿過那簾子,便是一處水霧缭繞的空曠之地,入眼一片青白,地上有雨後積水,一路鋪展着,向着不遠處高聳的漢白玉宮阙。
青婀遮手眺望,面露驚喜:“哎呦喂這個看着很像是希臘聖域的黃金十二宮啊!
第一宮的穆先生在哪裡?
!
”
有一人一襲白衣,抱琴站在宮殿門口。
老宋拍大腿:“看這造型!
一定是個潔癖!
”
“你們來了。
”那人一開口,那一管語音清澈沉雅,好像一曲天音,仙樂翁翁,疊雪踏雲而來。
這一聲話語如韻白,将那簾子那頭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都滌蕩殆盡,肅清了所有的激越波動,隻留下一地好像是剛剛下完一場豪雨的淺水,清澈,甯和。
玉卮和蔓藍面露喜悅:“呀,還是個男神音!
”
鬼王姬摸着下巴思忖:“這人看來身手不錯,那個琴那麼重,他抱着還沒啥反應。
”
今昭還在迷糊:“從發型來看,穆先生不太像吧……”
老宋也跟着攙和:“總比阿布羅狄強。
”
老元不服:“胡說,迪斯馬斯克才是喪病。
”
今昭搖頭:“我覺得阿魯迪巴最悲慘。
”
元夢澤在一旁忍俊不禁,但還是收斂了笑意,轉向那人:“宮先生,朱橚已經到了。
”
那人斂衣一禮,語音清雅:“我是天音宮韻白,勞煩諸位了。
”
“你助我們來到明朝,找到朱橚,還加快了時間進度,所為何事呢。
”朱師傅開口問。
“為了修複清平館。
”宮韻白開門見山,“我的七天之前,從百裡燕處聽說,有一位故交将要出山,于我和我的朋友們不利。
清平館是唯一庇護之所。
我們沒有時間等待地龍的修複,因此隻能走捷徑,求助玉族。
”
也許是這份開門見山的解釋博得了一貫毒舌的老周的好感,老周這次倒是心平氣和:“我們實際上,已經和朱橚相處了六十年,是不是?
”
宮韻白點頭:“不錯。
加快的是你們的感覺,并非是實際。
”
“那還要多謝你了啊。
要不然在明朝混六十年我想想也覺得萌萌哒。
”青婀拱手。
“既然人已經到了,就請久坐,讓我用琴曲送他一程。
”宮韻白說着,就要把琴放下。
“等等!
等等!
”利白薩喊道,“我是怎麼回事啊!
我當時穿越到民國之前,聽到的琴音,是不是你啊。
”
宮韻白淡淡掃了利白薩一眼,回答:“是的。
你與我的朋友,屬同相類。
衛先生則出身六合。
至于王子喬,好久不見了。
”
酒吞扯出一個笑來,陰仄仄地看着宮韻白:“我說是誰,原來是你這個小屁孩。
當年趕着百裡燕叫妹夫,趕着我叫姐夫,而今還叫麼。
”
宮韻白也笑了:“我叫的那人,在五百童子死去之時,便也死了。
”
兩人眼神刀光箭雨,老周抄着袖子打斷:“能不能先幹活,再撕逼?
”
宮韻白看了看老周,突然又一笑,笑得老周心頭發毛。
可琴師大人已經悠然落座,彈起了一首琴曲來。
那一首曲子,是《念奴嬌》,配上宮韻白的唱詞,卻是張孝祥的一首《過洞庭》,隻聽那清雅之音徐徐唱:“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
“玉界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
”
彼時中都留守,卻深知雖然備受母後疼愛,可因天生鬼眼,注定孤獨。
“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裡俱澄澈。
”
我心中自有理想,可天賦異禀,屢屢遭人忌憚,唯有她,那次相遇,令我覺得,一生終有知心交付,從此天高地闊,任我憑說。
“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
那時兩小嫌猜,那時執手偕老,那時相伴歲月,其中甜蜜滿足,又何足為外人道也。
“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
”
良辰美景終有時,從此千山暮雪,隻影向誰?
“短發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
”
天大地大,我自獨行。
“盡挹西江,細斟北鬥,萬象為賓客。
”
天大地大,我還尚可一覽顔色,不負此生。
“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
一生之中,來去無數,迎來送往,一路向前,沒有終點,有的隻是一路上的風景,這邊是歲時十二族的宿命。
我的宿命。
琴曲終了,朱橚睜開眼睛,或許是他此刻正置身六合的緣故,因此并沒有褪去玉殼,而是整個人輝煌晶瑩,如一尊玉像,伫立在琴曲繞梁餘音之中。
許久,他轉身,微笑:“諸位,這幾十年來,有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