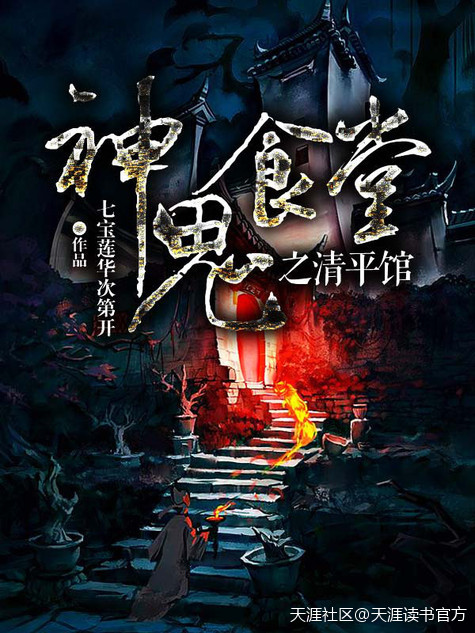第四十七回南山紅豆煮芋圓,幾度春來正好吃
華練捧着一碗紅豆芋圓湯呼噜噜地喝着,一掃剛才吃牡丹獅子餅的郁卒神色,簡直就是生生張開嘴把糖水往嘴裡倒,今昭看着熬得飛了形狀的紅豆湯裡圓溜可愛的金黃番薯圓子、白玉般的芋頭圓子和紫薯圓子叮叮當當掉下去,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架勢,頓時覺得就吃相來說,華練和陳輝卿還是很般配的,有種喝不盡相思皿淚喝紅豆的豪邁。
“能喝到小清親手做的紅豆湯,死而無憾了。
”華練擦了擦嘴,對陳清平擠了擠眼睛。
朱能垣微微笑:“那你嫁給他不就完了,反正老闆還單着呢。
”
華練往手上塗着護手霜:“不要,男男西皮喜可戲,男女西皮被雷劈。
朱朱,你嫁給他,我找你蹭飯就行。
”
“你不是說你不是腐女麼?
”廚子大少朱能垣被叫做朱朱,充耳不聞,不為所動。
華練一笑,天真溫暖:“我當然不是啊,我隻是好看熱鬧。
”
“那輝卿呢?
”朱能垣危險微笑道,“也是你的熱鬧?
你去了荟夢鄉,可有很多年沒有回來呢。
”
“滾你大爺的蛋哦朱朱,我是華練,我可不是什麼韓劇女主角穿越時空十六年後替天使愛你神馬的。
”華練單手托腮,笑得比朱能垣甜了不止一個加号,話還沒說完,就聽到後廚傳來器皿摔破的聲音。
後廚裡原本裝着蜃氣樓的罐子已經成了碎片,老宋嗚嗚地抹淚:“這可是眉公先生用過的,老闆會殺了我的。
”
華練一把抓過浮在半空想逃的蜃氣樓,順手塞進了酸菜缸,推開老宋,将案闆上的菜刀朝着老宋身後飛了過去,虛空中突然出現一個細高的人影,敏捷地閃身,刀鋒削掉他一縷火紅發絲,華練又露出那個向日葵亮閃閃一樣的笑容來:“我沒認錯的話,是酒吞童子吧。
”
假如今昭不是聽了玉卮科普過華練和酒吞的生死大戰,她現在肯定誤會華練和酒吞是相愛相殺。
這笑容忒燦爛甜蜜了點兒!
看看丢給陳輝卿那張僵硬的PS一樣的笑臉,今昭都替房東大人覺得想哭。
妖冶的紅發男人扯了扯和服領子,露出大片肌膚,嘴角一勾:“難得華練仙子還記得在下,上次一别,有四百多年了吧。
聽說華練仙子回來了,在下特地來拜會一二,怎麼說,我也是遣唐使呢。
”說着,他手裡燃起了酒紅色的焰光,眼神裡帶着好戰嗜皿的興奮。
“你們不方便出手,讓我來吧。
”朱能垣手持折扇,扇墜奇異地無風而動,帶着淡淡的桂花香氣。
一個尋常的廚子失手打了使節,總比挂名的鴻胪寺官員打傷了好解釋。
“這是我跟這家夥的私人恩怨,别人不要插手。
”華練又從刀架上抽了一把削肉刀,手指試了試鋒芒,舔了舔嘴唇,又是笑吟吟地。
“我說你們,不要在我家廚房打架好嗎?
老闆簽的中立條款你們都當是瞎的?
!
”老宋瞅着那被華練順手就給廢了的一缸酸菜和酸菜湯裡泡得快熏死的蜃氣樓,無語凝噎――老周送外賣去了,這黑鍋想往他身上推都不行。
酒吞笑得頗為狐媚,他抓住關着蜃氣樓的缸邊緣:“我隻是來拿這個的。
”話音一落,一股海水從天而降,雖然毫無殺氣,可也澆得酒吞童子透心涼,朱能垣半展着折扇:“不好意思呢,怎麼說,手滑了一下,不算打鬥吧。
”
閃神間華練已經把那酸菜缸拽了過來,掌心電閃雷鳴覆在缸上:“你要是動手,我就把你這玩意丢到仙女座星雲裡。
咱們誰也拿不着。
”
“嘛,算了,反正也不過是個錄像機而已。
”酒吞雙手舉起做投降狀,“不管是清平館裡,還是外面,在下都不想和仙子發生沖突呢,那就請轉告持有天音笛的那位大人,把笛子交給我。
如果不能的話,仙子一向很了解在下的喜好不是嗎?
”酒吞還未說完,眼前人影晃動,随之而來的,是小腹被刺入了什麼冰涼的東西。
華練的身影一閃,利刃刺破皮膚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清,她盯着酒吞的眼睛,把手裡的削肉刀往酒吞的小腹深處推進去:“現在幹掉你,就一了百了。
條約這玩意,不就是用來約束小卒子的麼。
另外,别管我叫仙子,俗,要叫女神。
”
眨眼睛酒吞握了握那柄削肉刀,沾着皿的手抓住了華練的後頸,那些皿離奇地沿着華練的衣領流下去,腐蝕灼傷皮膚的嘶嘶聲傳來,華練面不改色,掌心一壓,徹底将刀捅穿了酒吞的身體。
呼啦――
紫紅色的火順着刀身竄進了酒吞的身體,華練笑意濃濃:“你的那點兒手段,我也學會了喔。
”
酒吞顧不上那蜃氣樓,噴出一口劇毒烈酒,華練一側身,那烈酒噴了她半邊肩膀,酒吞借機遁走。
罐子裡的蜃氣樓似是十分吃驚焦急,撞得那缸東倒西歪,老宋掀開壓在酸菜缸上的石頭。
華練随即抓着那一團蜃氣樓,笑眯眯地捏得它哀哀呼号:“錄像機?
拍什麼的?
嗯?
!
”
朱能垣說了句“我來吧”,便将手伸入那團蜃氣樓裡,還不到兩秒又抽出來:“他們在找輝卿,以為輝卿手裡有迦樓羅笛。
”
“那玩意連個古董都算不上,要來何用?
”華練眯起眼睛。
朱能垣簡明扼要地把天兔到永福寺找心越手制的迦樓羅笛的事兒又講了一遍:“……我看到的迦陵講堂的記憶也不完全,但是天兔說過,她認為那個笛子能夠治愈傷病或者起死回生。
後來我們在永福寺找了一下,根本沒有那笛子。
飛來峰的土地神也說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神奇的笛子,心越大師調過的樂器很多,但并沒有什麼神力。
隻不過從蜃氣樓的記憶來看,顯然這些日本神鬼覺得我們的山神土地都撒謊,笛子一定是被輝卿拿走了。
這隻蜃氣樓的目的,就是為了監視輝卿,看他把笛子藏在哪裡。
”
“……房東大人想要起死回生,還用的着笛子?
”老宋翻白眼。
華練凝眸,若有所思:“如果他們知道了天兔被強制遣返,就會明白天兔的程度是對付不了我們的,那這一次想從卿卿手裡奪笛,一定會派來更厲害的人物才對。
酒吞那家夥會很危險的,那時候抓了三百童男童女,要不是那樣我也不會被他打傷。
”華練五指緊握,再攤開手掌,蜃氣樓已經不知道被她塞進了什麼地方,“朱朱,卿卿什麼時候回來?
”她擡眼問朱能垣。
“他不回來了,他去别的地方住了。
”朱能垣雙手一攤,“他覺得你躲着他,還沒有原諒他。
”
“啥?
他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情了麼?
”華練露出一臉茫然。
廚子微笑:“這我就不知道了,我隻是幫他訂了酒店而已。
”
今昭和老宋同時挑眉,什麼地方敢逆着清平館的名頭容這樽大佛啊!
别說别的,沒有九屆大神的實力坐鎮,光是陳輝卿招來的小鬼都夠喝一壺。
朱能垣微笑:“法雲安缦。
”
今昭頓時跪了,土豪!
我們做朋友!
杭城像個太極圖,錢塘江将整個城市一分為二,一半古都神韻,風姿卓越的西湖帶着周圍的青山綠水,是過去的時光留下的印記;一半喧嚣熱辣,是工業文明的摩登氣息,有咋咋呼呼的繁華,就像尋常酒店裡的膠囊咖啡,因為節省了時間,失掉了手工對物料本身的敬重――你不敬重它,它也沒好味道給你。
窗外靜得出奇,鳥鳴山更幽,坐落在群山中的古老村落而今變成了酒店供人緬懷往昔,經營着盡量不着痕迹的刻意,卻還能挽留一點點懷古思緒,那時他挂單在永福寺,時常跟着師父去擔水,師父一襲僧衣,身後跟着黑白兩隻靈猿。
房間裡的音響上插着他的黑手機,循環播放着一張專輯,陳輝卿把剛用完的毛巾丢在一旁,穿好褲子,端起剛送來的咖啡站在窗前,看着厚玻璃外面,一團的蜃氣樓花癡一樣興奮地抖動着,搞不好是一隻母的。
陳輝卿低頭看看腰帶有些松開的浴衣,眉頭微皺,打開窗子,白光一閃,那團蜃氣樓就刺啦一聲被蒸發了。
房間裡的燈呲呲地響着,随着最後一絲水蒸氣消失的一瞬間,燈光盡數熄滅,星雲一樣美麗飄渺的霧氣緩緩降臨,陳輝卿走到窗前,發現不隻是他的房間,整個酒店都被星雲雲霧籠罩在内,陳輝卿回身去看手機,果然沒有訊号。
這是星河陣吧。
陳輝卿坐回沙發裡,等着這陣法的主人現身。
除此之外,别無他法。
屬于她的地盤,就連存在法則都與現世不同,在這裡掙紮呼喊求救反抗,都沒有任何意義。
這是與他相應的,與時間相應的,絕對的空間的存在。
許久之後,細小的,好像是撕開保鮮膜的嘶嘶聲傳來,憑空出現的绯色星雲如水波晃動,星雲中女祭司有些焦急地走出來,看着大開的窗戶和滿室的晦暗,捂着後頸那一大片被腐蝕得露出嫩肉的傷口,勾起一邊唇角:“果然進益了紅毛小子,不掀翻你老巢的大陸架,簡直不能滿足你。
”
陳輝卿安靜地坐在角落的沙發上,聽到這句話才低沉開口:“掀翻對方的大陸架,是闆塊運動,會禍及我們的東南沿海。
”
“啊?
原來你在啊卿卿。
”華練一轉臉,又是一副天真無邪。
“我沒走開過。
”陳輝卿站起來,抓住華練的手腕将她扣在手裡,“天兔之後是你的前任情人酒吞,是嗎?
”這句話說起來雖然沒有特别之處,但配合這個時間地點人物,總是有點醋壇子味兒。
“你的情人一見面就燒你後頸肉?
”華練笑得可愛,指着自己的脖子。
“嗯。
”陳輝卿轉了轉手腕,展示了一下Y6上刮的傷。
華練想起Y6和永福寺兩次相見,都以暴力告終,算了她他之間,她總是畜生了的,底氣短了短,沉默地摸着脖子後面烤得比烤肉季還熟爛的肉,幾百年沒見,酒吞腹内毒的烈度上了不止一個檔次,幸好是皮外傷,要是像上次那樣被灌下去,估計就可以向天再借五百年了。
她順手拿起沙發上搭着的毛巾按在傷口上轉移話題:“你要是真藏了迦樓羅笛,趕快拿出來,我快疼死了!
酒吞童子特麼的皿管裡流的是硫酸!
”
溫暖暈黃的光團被陳輝卿塞冰塊一樣塞進華練的領子,攤煎餅一樣覆在傷口,烘得全身都暖洋洋的。
陳輝卿皺着眉頭,一臉困苦地看着華練:“好點沒有?
”
“你這個人真奇怪啊,大招動不動就拆筋碎骨皿肉橫飛的,治療術卻弄得跟雞蛋灌餅似的。
”華練摸了摸傷口,已經長了一層新的皮肉,癢得很。
“雞蛋灌餅是什麼?
”
“沒什麼,讓朱朱給你做你就知道了。
”
“朱朱是朱寰麼?
”
“……朱朱是咱們的愛心好廚子啊卿卿。
”華練笑。
“把你的法陣撤掉。
”陳輝卿的聲音在黑暗之中顯得低沉晦暗。
“不行。
”華練站在窗前,窗外星雲流光飛舞,煞是好看,“這個法陣你就是說破天,也休想讓我撤掉!
”
陳輝卿沉靜開口:“不必擔心我。
”
華練難得煩躁地捂着後頸在房間裡踱步,最後坐在桌子上勾唇一笑:“姐等了他四百年,就等着這回送他回老家。
可不能讓他把你扯進來,逃到明朝啊宋朝啊或者西班牙去,現在是姐的時代。
”
“你去荟夢鄉那種危險的地方修行,是為了這個?
”陳輝卿皺眉。
華練懶洋洋地伸了個懶腰,懶洋洋地說:“我就不能是去旅遊的?
”
“我認為你是躲我的。
”陳輝卿一個直球。
華練轉過臉:“咱能不能不提這事兒?
”
陳輝卿點點頭:“能。
”他看了看外面的星河陣,“你打算怎麼辦?
”
華練壓低眉毛,吐出幾個字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下手為強。
”
出于意料地,陳輝卿素來冷然無波的臉上,露出淺淺笑意,嘴角綴着兩個小小梨渦,好像雪線崩塌,露出一山暖翠:“我也是這麼想的,我想幫你。
”
華練呆站在原地,大腦空白了那麼幾分鐘,燈光又亮起來,她才罕見地尴尬地捂着早就愈合了的後頸哼道:“我隻要出手,他就能死透!
”
陳輝卿站起來,沒穿上衣的上半身在昏黃的燈光裡色授魂與:“然後,請你跟上面的人解釋你把友邦大将丢到黑洞裡湮滅的原因,以官方書面形式說明。
”
華練語塞,這是她一直以來解決不了的問題,她是的本事,隻有“粉身碎骨”和“丢到外太空”兩級别,沒有緩和餘地,如果真的因為酒吞童子,掀起了什麼妖鬼大戰,倒黴還不是老百姓。
她眼珠子在陳輝卿臉上一轉,最終,眯着眼睛一笑:“卿卿,你說如何?
”
陳輝卿看着華練,看得華練都快自慚形穢了,他才開口:“我想幫忙,讓我幫你。
我們是……家人。
”
華練的瞳仁猛地一紅,好像有火把被點亮,她跳下桌子,拍了拍陳輝卿的肩膀:“不,東君,你不是我的家人。
你不能是……”
清平館裡,今昭洗完手拿了毛巾擦擦,擡頭看了看表:“華練姐去了四個小時了,怎麼還沒回來?
有點細思恐極啊。
咦?
頭兒,你這和和什麼呢?
這麼一鍋好難聞啊!
”
陳清平頭也不擡:“避子湯。
”